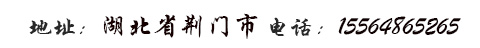在路上苍茫与寂寥秋日的呼伦贝尔
| 整个年,因为疫情和生娃,我窝在合肥,哪里也没去成。今年,疫情稳定了,娃也大了些,我也开始恢复了一言不合就出发的节奏。对于总是身处于固定场所的打工人,旅行和读书一样,是灵魂的一种放飞。短途长途皆可,一年总要逃离个几次,才能保证精神的旺健和感觉的新鲜。今年4月去了上海,回来老老实实坐了几个月的工位,又按捺不住想要出发的心情。9月,是时候请个年假,来趟远行了。想去云南,可云南还有疫情;想去新疆,又忐忑一岁多的孩子能否驾驭旅途的奔波和复杂的环境。最后,也是很随意的,就定了去内蒙古呼伦贝尔。一是没去过的地方都想去,二是觉得草原路应该好走,三是认为秋日的草原和大兴安岭也别有风情。九天八晚之行,来到这么偏远、辽阔而且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我以为我会有很多耳目一新的震撼体验。然而,一切竟然让我觉得再熟悉不过。熟悉的城市建筑风格,熟悉的冷空气,熟悉的大碴子东北话。我后知后觉,呼伦贝尔虽然属于内蒙古,但地理位置上,却处于标准的东北地区——大公鸡的鸡冠附近。我认为我是去了一个假的内蒙古,一个真的黑龙江。一路上,所有人说的都是东北话,东北菜到处都是,满洲里简直就是一个加强版的哈尔滨。当饭店的老板娘端上一盘锅包肉时,我才意识到,阔别8年,我又回到了东北。而这次,比我呆过的哈尔滨竟然还要再北一些。这次旅行,我们的时间很充足,行程安排的很松散。一天只跑一二百公里。有时候甚至一天一个景点也没去,在蒙古包附近骑了个马,在莫尔道嘎爬了个不要门票的小山,这就是一天的安排了。如此佛系的旅行,以至于妈妈偶尔会发出质疑,我们今天就在这了吗?不过,每顿饭都是现成的,每餐饭后都不要洗碗,这样轻松的日子无疑是让她舒心惬意的。因为时间充裕,所以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海拉尔、额尔古纳湿地、根河、莫尔道嘎、室韦口岸、恩和俄罗斯民族乡、边防公路、黑山头、满洲里、国门、套娃广场,当然,还有茫茫大草原,都没落下。不知是因为疫情带来的旅游业的萧条,还是东北小城市人口的大量流失,又或是夹带了北方秋天的萧索。这次呼伦贝尔之行,最突出的感受竟然是苍茫和寂寥。连绵不断的草原、层层叠叠的大兴安岭,没错,是美丽壮观的。然而,看得稍久,就有一种审美疲劳和乏味。尤其是阴天,不见光线,没有人烟,这硕大的天地反而像被什么罩了起来,有种窒息感。站在山顶,俯瞰莫尔道嘎,这座大兴安岭的小城,星星点点的板房,尽收眼底。板房院子里堆着高高的木材,年轻时候去南方闯荡过的男子已成了年近六十的大叔,在这里经营着一家铁锅炖饭店。三个孩子,两个已成家,一个才6岁,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这座寂静荒凉到让我觉得窒息的小城,大叔却安之若素,还自信满满的推销自己的人生哲学:“攒钱干啥,攒钱没用,要攒人!”方才我还在想,是什么样的人愿意一辈子住在这样闭塞的地方?这里的孩子长大了又会有怎样的生活?而后我又明白,人本来就不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之路。离开莫尔道嘎,我们又来到了中俄边境小镇室韦和俄罗斯民族乡恩和。边境小镇很有特色,房屋都是传统的俄式木刻楞。木质房屋和地板,尖尖的房顶,窗户边多会放盆花。胖胖的俄罗斯族姑娘,长了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张口却是地地道道的东北话,经营着一家名叫“阿丽莎”的小饭店。身边呼啸而过的骑着电瓶三轮车的大叔,小超市里唠闲嗑扯家常的大叔,慢悠悠的从屋子里走出来包着头巾的老奶奶,都还有着明显的俄罗斯人面部特征。历史上边境地区的通婚,产生了第一代有着“中国爸爸,俄罗斯妈妈”的俄后裔们。随后,他们世代在此聚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和文化。可惜的是,疫情夹杂淡季的影响,有一半挂着招牌的商户都关门了。如此有特色的小镇,也没有了生气。这里的白天和夜晚,都是静悄悄。当然,旅行途中也不乏有开阔、震撼和难忘的瞬间。登上边防公路旁的山坡,俯瞰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那种壮阔;站在满洲里巍峨国门下,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红字,那种庄严;在根河神鹿园,近距离接触驯鹿、梅花鹿和小羊、小兔,那种喜悦;在根河宾馆,看到房间床头柜上摆着的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那种惊喜;在满洲里大山俄货超市里看着满目零食而迷失自我,那种兴奋;在大草原上听着逃跑计划的《一万次悲伤》狂奔起来,那种酣畅。当然,带着父母和爱人,带着年幼的宝宝一起走走停停,点滴中,更有无限温情和满足。我始终认为,人生没有白看的书,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旅行都不虚此行,每一次出发都会有所收获。在这次旅行的路上,我读到很有感触的一句话,“不要担心生活不再出现丰富的情节,因为真正的情节在于内心的跋涉”。停滞的人生是对生命的浪费。做一个在路上的人,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ermopana.com/bempls/10648.html
- 上一篇文章: 呼伦贝尔市委书记于立新到莫旗暗访明查,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