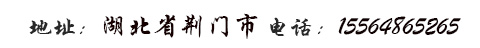将钱币扔进喷泉许愿的传统自何时形成
|
回到当下,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在电子支付日益流行的今天,我们与货币的互动虽逐渐脱离物质形态,但随之而来的是联系的日趋多元。除经济功能之外,货币也是一种交流的媒介,人们借此交换的不仅仅是价格信息,还包括信仰、权威、忠诚、欲望甚至是轻蔑。同时,货币还是一种纪念过去的方式,它在人、制度、神灵与祖先之间建立着超时空的连接,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变化。 从社会文化融合角度而言,现代西方货币观的起源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前七世纪,小亚细亚地区出现了最早的金银合金币。多少可能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货币诞生之初,其并非完全由公共权力机构制造。由于各地铸币并不统一,钱币兑换几乎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加之假币大量存在,试金员一度是社会必需的职业,他们不仅善于使用各种工具,还练就了听音闻味以辨真伪的本事。此外,在流通功能之外,钱币也日渐被赋予贮藏、丧葬,甚至献祭许愿等诸多仪式化意义。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货币文化史I》中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内容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货币文化史》(全六卷),比尔·莫勒主编,斯特凡·克姆尼切克编,侯宇译,贝页 文汇出版社,年6月(后四册陆续出版中)。 货币并不总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制造 在当代世界,货币的制造(以硬币和纸币的形式)是一种由国家进行的、受到高度保护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秘密的活动,我们倾向于把这种状况类推到古代。事实上,在罗马圣克莱孟教堂下发掘出的罗马帝国铸币厂也支持这一观点:该铸币厂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有着厚厚的墙壁,没有窗户。尽管这座建筑的外观一览无遗,功能也很清楚,但里面的情况却隐蔽得极好。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货币并不总是铸币,也不总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制造。在称重金属的前铸币时代,无论是东方或伊比利亚半岛的银或金,还是意大利半岛和可能在欧陆通行的粗铜(aesrude),除了保证共同的重量标准外(但采用共同的重量标准也可以是个人发起的结果),似乎没有任何公共权力机构参与。这些金属物品实际上是由私人制作的。 虽然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与古代资料一致),铸币是由公共权力机构生产的,但情况似乎并不总是这样。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吕底亚最早的琥珀金铸币是受国家垄断的。在前罗马时期的高卢地区,铸币分散化的证据似乎更加充分。这个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法国北部,于公元前年左右开始发行铸币。最初,它们的钱币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金质斯塔特的早期忠实仿制品,后来很快演变成了凯尔特风格的原始钱币。在公元前年左右,出现了铜合金浇铸的钱币。几十年后,一些地区的金币被银币所取代,这些银币通常带有受罗马风格影响的图案。当地的钱币,主要是铸造的青铜钱币,在高卢战争(公元前58—前51年)之后被广泛使用,但在公元前20/10年前后完全消失了。 纪录片《货币》()画面。 纵观这三个世纪,钱币的分布与各个civitates(拉丁语,常译为“部落”)的领土范围相一致的情况相当罕见。有些钱币(包括一些低价值的浇铸钱币)流通的区域很广,而另一些钱币只在一个地方出现。尽管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越来越多的钱币样式(cointype)上出现铭文,但在高卢战争之前,没有一枚钱币提到高卢部落的名称。甚至在此之后,大多数铭文也只有个人名字,其中有些是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提到的贵族。 这些证据说明,钱币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大部分)很可能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与在高卢发掘地出土的铁器时代铸币的生产痕迹非常吻合。在普瓦捷(Poitiers,位于法国)附近的米涅—欧桑斯(Migné-Auxances),人们在对一个农场的抢救性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公元前—前年的一处可能是铸币厂的残迹。铜合金币坯的生产是在一个深坑中进行的。虽然没有发现与铸造本身有关的工具,但很有可能也是在农场里进行的,因为币坯与发掘过程中发现的钱币的成分相似。 这证明了铸币厂是在生活区内运作的:毫无疑问,铸币被严格控制,但肯定不是秘密进行的。此外,技术研究表明浇铸和锻造——除了模具的雕刻之外——一般的工匠都可以做到,并不需要特别的技能。在出土的工作坊中,很明显可以推测,铸币并不是唯一的活动。雅典的官方铜币铸造厂中也可能是这样,因为在那里发现了铁器加工的痕迹。 雅典定下了雅典钱币的标准图像:正面是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的头像,背面是猫头鹰(一种与雅典娜有关的动物)和橄榄枝以及象征雅典的文字:ΑΘΕ。(出版社供图) 这少数几个例子与官方铸币有关。在日常生活中,非官方钱币的铸造更加深入人心。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我们处理的是否是假币,因为有些钱币非常独特,看起来不太可能造假。在这方面,罗马高卢的钱币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研究。有些生产地点确实是隐蔽的,比如在洞穴里。但大多数的生产遗址都发现于城镇、金属工作坊或乡村定居点中。这些非官方制作的钱币,无论其地位和铸造原因为何,似乎都出现在货币短缺时期(有时只是小面额钱币的短缺),这可以视为日常生活中对货币需求的明确标志。 因此,铸币的实际生产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通得多。据我们所知,其他形态的货币生产也是如此。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献中了解到一些可以用作货币的商品:金属(金、银、铜及其合金,也包括铅)、布料、食品,以及谷物(比如经常提到的大麦)。如果金属器物通常有可识别的形状,那么它们可能具有货币功能(如环形或异形锭),而且做成这些形状几乎不需要特殊的工艺。 希罗时期货币的贮藏与使用 罗马时代,大多数人会选择把钱放在家里。庞贝古城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罗马人是如何在家中存放钱币的。“米南德之家”(HouseoftheMenander)的窖藏储存在地窖中的一个大箱柜(arca)里,里面的钱币与珠宝被放在一个和其他生活器物分开的小盒子中。在隔壁一幢房子的卧室里发现了一些钱币串,每个人显然都把自己的钱包藏在了床下。由于维苏威火山爆发对保存古代世界证据的特殊性,这些细节虽很难从其他地方获得,但我们可以据此假设类似的趋向:贵重物品和大笔资金被安全地收纳起来,有时还被藏起来(这当然解释了现代屡次发现数目不详的窖藏的原因),而零钱则被放在比较容易拿到的地方。 四柱神庙的正视图;柱子之间是三位铸币人,上面有天平和羊角装饰,脚下有一小堆硬币。(出版社供图) 我们能够从古人保存和运送钱币的方式推测,他们是如何使用钱币的。有趣的是,在希腊和罗马时代,钱包似乎成为携带钱币最普遍的方式。这说明在当时随身携带一些零钱,既常见又有效,而且当时钱币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没有钱包能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是由易腐蚀的材质制成的,但在荷兰的巴赫尔—康帕斯库姆镇(Barger-Compascuum)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公元2世纪的皮革钱包。 在罗马时代还有将钱包设计成可以戴在手腕上的金属钱包的例子,有些钱包里还装有钱币,通常是铜币。更大金额的钱币也可以装在钱袋(拉丁文中“follis”一词的原始含义就是指钱袋,后来才表示钱币)或者不同大小的箱子里。在一些著名诗句中,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还曾写到雅典人把钱币装在口中。这显然非常不切实际,他笔下的一个角色甚至因此吞下了口中的零钱。 说到货币的用途,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支付商品和服务费用的功能,这也是它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交易可以在各种地方进行:商店、旅馆、私人住宅,当然还有集市。在考古发掘中出土钱币的密度和古代钱币的使用频率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例如,理查德·霍布斯(RichardHobbs)指出,在庞贝古城的VI1街区(insula)中,钱币更多地出现在街道、小商店周围和圣坛附近。这也许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为在前罗马高卢和罗马高卢也有类似的情况。 英美庞贝古城发掘项目发现的庞贝VI1街区的钱币分布图。(出版社供图) 萨伽拉索斯(Sagalassos,位于今土耳其)的两处市集为我们揭示了古代晚期城市市集中有趣的一面。这些市集是由小型房间围成的开放庭院,广场地面上标示了可移动的木质摊位。考古人员在各个房间和中央庭院中都发现了大量的钱币。这些市集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日常交易环境。 在萨伽拉索斯,通过对出土钱币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重构市集中不同房间的功能:大部分的房间似乎是零售店,有时与工作坊相连。在两个市集中,人们都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发现了称重设备和大量的钱币。这个房间可能是钱币兑换商的办公室。事实上,我们知道钱币兑换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古代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铸币从未统一过,使用者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钱币(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也有不同的铸币流通,尤其是在罗马帝国东部)。 再加上假币的存在,人们需要经常对钱币进行检验。比如雅典城有试金员(dokimastai)一职,负责在市场上检验钱币,他们显然是按日委任的。这项工作本身似乎是一门技术活,试金员不仅要会使用试金石和天平,还要懂得如何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听声音和闻气味来辨认钱币真伪。 赌博类的金钱游戏在古代就已经非常盛行,在公共广场上经常能看到雕刻的游戏棋盘。庞贝的涂鸦证明,城镇和市集还发生过频繁的借贷和典当行为,尽管涉及的金额可能非常小。虽然这些交易确实有记录,但典当和借贷肯定不是专业人士所为。这也证明当时处于城市社会中下层的人需要一定的现金来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们的文献记载提到的大多是城镇,但我们不应低估钱币在乡村的使用。埃及的纸莎草文献表明,我们通常说的村民习惯于“自然经济”的传统假设是错误的。 钱币的另一种用途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ermopana.com/bempdt/11574.html
- 上一篇文章: 日语中国家名称词汇五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