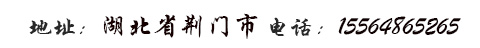玛雅造境记
|
中科白癜风医院荣获安全管理优秀奖 https://4001582233.114.qq.com/ndetail_4852.html 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 ――(德)荷尔德林 论起“诗意地栖居”,大概鲜有能与古玛雅人比肩者。 隐匿在热带丛林深处,侣虫鱼,友鸟兽;饮山间之坠露,啜日月之精华;佩羽毛之繁饰,折琼枝以焚香;书陆离之秘符,揽玄妙之造化。对于“久在樊笼里”的现代人,玛雅人的诗意带着一缕归隐的浪漫和羽化的仙气。 这份诗意的关键在于造境。意境三分,一分天意,二分人谋,睿智的玛雅人将栖身之所打造成“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秘境。 (一) 秘境本是天成。它们诞生于造物鬼斧,散落在世外桃源。幸运的玛雅人碰巧找到了,并在其中安了家。 一马平川的尤卡坦半岛西侧第一座凸起的山头坐落着玛雅遗址Palenque。站在遗址高处俯览平原,好比于天涯观海,只见霄壤浑然一体如晴天时的海天一色,空气仿佛被海拔赋予了水的质感。若有千里眼,甚至可以眺望ChichenItza遗址金字塔的顶尖。 墨西哥玛雅遗址Palenque 在Palenque的高处俯瞰 将目光收回,近处更是别有洞天,雨林植物搭建起空中楼阁,亭亭乔木用巨伞擎起天空,低矮灌木在其荫蔽下摇曳生姿,藤蔓植物迂回其间,像牵线,传递树间密语,又似搭桥,架起吼猴的高空走廊,连最不起眼的青苔也不甘示弱,在石阶上成片蔓延,试图将绿地毯织得更密一些。 遗址中既有山的沉稳,也不乏水的灵动。几股山泉依山势,疾行时成瀑布,歇脚时成清潭,大多时候拧成一条汩汩流淌的河。在遗址中穿行,水声不绝于耳,给人一种雨天的幻觉,久了易被催眠。水声粗听单调重复,细听又变化无穷,倘若在一个晴朗的夏夜踞此倾听,定会迸发“逝者如斯”的生命玄想。耳得为声,目遇成色,偏安一隅却独拥居高临下视角,远离尘嚣而寄情山水余韵悠悠,这的确是一处天然诗境。 Palenque的瀑布 Palenque需要跋山,访另一处玛雅遗址Yaxchilán则要涉水。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河Usumacinta西岸一个章鱼状半岛上,Yaxchilán须得坐船抵达。 船如长梭,在浑浊的河水中行驶得并不快。船夫时而停船指给我们看岸边的鳄鱼,不过,那究竟是色泽似石头的鳄鱼还是形状像鳄鱼的石头,我终也没分清楚。河的两侧虽迥然两个国度,风景却不分家,皆是茂密的植被,有的似林中野人,蓬头散发;有的如玛雅贵族,临流自鉴;有的像史前巨兽,垂头水中,开怀痛饮。 边界河Usumacinta 河对岸的危地马拉 河对岸的树似人 当船驶近章鱼状半岛时,无心的一瞥使我顿时心花怒放,像是满足了一个夙愿——我如考古学家般“发现”了岸边一座金字塔,“犹抱丛林半遮面”。 其实,在雨林深处“发现”一座金字塔是大多数金字塔迷的执念。只可惜,很多遗址的设计缺少这份浪漫,通常是步入遗址,没经过几棵树的情感过渡,扑面而来就是一座金字塔。在这点上,Yaxchilán别出心裁,深谙造境之术,不止一次投合了访客的心意。 继行船途中的“发现”,进入遗址后,我在幽阒雨林小径尽头又“发现”了一座小型金字塔,只见树丛和杂草围成一圈,聚光灯般点亮中心一座金字塔,有如万绿衬红、众星捧月,从此这一场景定格为我在墨西哥所见最经典的一处,已故的著名美国考古学家MichaelD.Coe也正是在此留下一张令人难忘的背影。再一次惊喜是当我在山间穿行疑无路时,头顶方向却猝不及防地豁然开朗,一簇玛雅建筑在树叶背后闪光。 第一次惊喜——行船途中发现岸边一座金字塔 第二次惊喜——进入遗址,一段雨林小路的尽头又是一座金字塔 第三次惊喜——山间行走疑无路时,头顶上方忽现玛雅建筑群 Yaxchilán也是一处山水秘境。尽管以现代文明的眼光看,此地未免偏远,连路都不通,但在当时则不然,这个邦国依河而建,河既是天然的路,可以发展贸易,又是天然屏障,用以防御入侵者。 Palenque和Yaxchilán只是上千座玛雅遗址中的两处,更多已知或未知的秘境仍遗珍散珠般隐匿在中部美洲热带地区,绰约如处子,各美其美。除了林立在山间的,蜿蜒在河畔的,还有蹲伏在盆地的,如危地马拉Petén盆地中的遗址Tikal;也有延展在平原的,如尤卡坦半岛上的遗址ChichenItza;甚至还有守望在海边的,如墨西哥的遗址Tulum、伯利兹的遗址Cerros。 墨西哥玛雅遗址ChichenItza 墨西哥玛雅遗址Tulum(网络图片) 伯利兹玛雅遗址Cerros(网络图片) 玛雅邦国的选址既考虑审美也兼顾实用,例如交通。玛雅文明早期,贸易多通过陆路,因而富饶起来的是内陆邦国,如危地马拉的Kaminaljuyú,它曾控制着从墨西哥中部高原一路南下至墨西哥湾的重要通道。玛雅文明中期,随着尤卡坦半岛玛雅邦国的崛起和中部高原帝国的衰落,水上贸易盛行,一些国家临河而建,如Yaxchilán。其实,自Yaxchilán顺流而下40公里,河的对岸还有另一处遗址PiedrasNegras,与其遥相呼应。由此想见,当年这两个玛雅古国如一对孪生兄弟,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共同主宰着这条河的通行。玛雅文明后期,海运也极为发达,据说当年哥伦布来美洲时曾在洪都拉斯北岸遇到过满载土特产的玛雅商船。 (二) 天意既赋予了古玛雅人秘境,如何铸就“境中之境”则靠人谋,而玛雅建筑在自然诗境之上又添了一分仙境。 如果说,中部美洲高原文明的建筑占地广袤、气势恢宏,好比宋词里的豪放派。那么,玛雅建筑则精致秀美,盘盘囷囷,如丛林中走来的一首婉约小令。 玛雅建筑常常成簇地长在一块巨型地基上,远看像极了城堡,虽远不及欧洲城堡那般华丽对称,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从容。我曾在墨西哥玛雅遗址Toniná见过最震撼的一座:走过一段低坦的山间谷地,一大簇城堡峨然逼现在眼前,高下相拥,令人怀疑是哪里的愚公移来了一座山。缘阶而上,在不同高度散落着广场平台、屋舍残垣,所见风景也迥异。最终,沿着陡陡斜斜的石梯,手脚并用,可以登至城堡众多塔峰中的一座。站在玛雅世界的制高点仰观宇宙,俯察品类,我今日所见山之轮廓、地之肌肤,又与千年之前古人所见有何异同呢? 墨西哥玛雅遗址Toniná Toniná城堡“远近高低各不同” 其实,这种城堡式建筑更像是金字塔的某种变体。传统金字塔是一个棱锥体,仅在顶尖立一座神庙,如中部高原特奥蒂华坎遗址的太阳金字塔。而玛雅人的城堡似乎是本着实用性原则对传统金字塔进行了改良,在塔身的不同高度分出平层,筑建屋舍,拓宽空间,好似在礁岩上层层附着的牡蛎壳。 攀爬在错落有致的城堡断阶上,逡巡在曲折迂回的石屋古廊里,真希望来一次彻彻底底的迷津,那便可以穿越回千年前的玛雅盛世。只可惜最终还是走到了出口,又回到没有神话的现今。 玛雅建筑之“仙”还体现在建筑样式上。很多玛雅神庙都佩戴一顶“石冠”,似束在玛雅人发髻上的羽冠。最经典的石冠在Tikal遗址,像是仍嫌金字塔不够高似的,古人又为塔顶神庙顶上加顶,而这人间制高点自然是留给权威的——石冠上镂刻着君王或是神灵像。 危地马拉玛雅遗址Tikal(网络图片) Tikal神庙高耸的石冠(网络图片) 这些石冠大多与神庙等高,有的甚至是庙身的两倍,需要当时建筑师高超的数学功底,才能避免建筑因“头重脚轻”而倒塌。脚踩金字塔顶的有限空间,头顶比自身还重的石冠,玛雅神庙夹在中间,内部空间小得可怜,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一个窄窄的走廊。然而,就连这走廊也并非全整,上方空间又被削去了一大半——玛雅房屋的顶部成尖拱形,即墙砖每高一层都往中间缩一截,于是,空间愈往上愈窄,最终汇合处则由一块方石支撑。不仅房间如此,很多门的造型亦如此。“尖拱”是玛雅建筑独特的设计,像指向碧空的大箭头,暗含天启。 玛雅房屋内部的尖拱 Toniná的三重门 还有的玛雅建筑简直仙得发幻,外观竟然是一张凶神恶煞的怪兽脸!令人想到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饕餮,而它那龇满獠牙的大嘴正是建筑的门,令人望而却步,具有“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威慑力。大概,古人每次踏进此门正是完成了一次对巨兽的献祭。 墨西哥玛雅遗址Chicanná的巨兽建筑(网络图片) 玛雅建筑风格虽整体统一但也有地域差别。以危地马拉Petén盆地为中心,在Tikal修长的金字塔风格基础上,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流派。 一种流派朝着实用方向发展,如以Yaxchilán为代表的Usumacinta河域风格,其最大特点是将Petén神庙上实心石冠改成镂空的,这大大减轻了神庙的负荷;又如以洪都拉斯遗址Copán为代表的Motagua河域风格,它追求相对低矮的建筑,很多干脆舍弃了华而不实的高冠。 墨西哥玛雅遗址Yaxchilán的镂空石冠 另一种流派则走向审美的极端。玛雅文明中后期,尤卡坦半岛上似乎掀起了一场玛雅世界的“文艺复兴”,从中可以看到Petén的古典光影,如南部Bec河域流行一种比Tikal更颀长纤细的金字塔,塔身甚至陡到无处立足攀登的程度,纯粹沦为装饰。北部Pucc地区则选择在建筑外观上做文章,创造了一系列几何马赛克,有的似希腊回纹,有的是雨神面具,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为Uxmal。 墨西哥玛雅遗址Xpuhil无法攀登的金字塔(Bec河域风格)(网络图片) Xpuhil的复原图(网络图片) 墨西哥玛雅遗址RíoBec(Bec河域风格)(网络图片) 墨西哥玛雅遗址Uxmal的建筑纹饰(Pucc地区风格)(网络图片) Uxmal建筑上的几何马赛克(网络图片) 墨西哥玛雅遗址Kabah的雨神面具墙(Pucc地区风格)(网络图片) 墨西哥玛雅遗址Labná带纹饰的“胜利门”(Pucc地区风格)(网络图片) 玛雅文明发展到后期,建筑风格不再纯粹。由于墨西哥中部高原文明Toltec的入侵,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建筑大量融入了高原元素,如ChichenItza武士神庙中的Tula风格武士柱。 ChichenItza的武士神庙 (三) 古玛雅成大事者亦拘小节。既已用建筑勾勒出秘境轮廓,他们又不厌其烦地充实每一处细节,那些点缀其间的石雕、壁画构成了玛雅的“微秘境”。 石雕艺术贯穿整个中部美洲文明,玛雅也不例外。很多石雕置于建筑物外观最显眼的位置,昭示古人来者盛世之况。其中最著名的当属Copán的文字石阶,两千多个的玛雅文字,整齐地镌刻在金字塔台阶外壁上,使登临者每一步都有如历史般沉甸甸。 洪都拉斯玛雅遗址Copán的文字石阶(网络图片) 有些石雕嵌在建筑物内饰中,例如门楣,即大门上侧的方石。很多玛雅门楣上刻有文字或图案,有的显露在外侧,像某种复杂的门牌标识,又似中国人贴在门框上的春联;有的则藏在门楣正下方,需要人进门时扭头仰望,这别扭的动作仿佛是在履行某种古老的仪式。玛雅最精致的三块门楣来自Yaxchilán,上面刻画了当时的统治者,介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不论工艺还是想象力均是一流的。这三块门楣如今都远离遗址,一件藏在墨西哥首都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另两件则远渡重洋,辗转至大英博物馆。从风格来看,它们约是出自同一位雕刻家之手,如今,石雕纹路清晰依旧,但背后那个堪称玛雅世界最伟大的雕刻家的脸却早已模糊,甚至连一笔名字都没有留下。 Yaxchilán门楣下侧刻满文字 Yaxchilán24和25号门楣,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网络图片) Yaxchilán26号门楣,现存于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还有些石雕孤零零地立在空旷之地,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纪念——或许是某位君王的登基,或许是某场战争的胜利,或许是某个时间周期的完成。玛雅世界中最大的石碑高达7米,重30吨,立在危地马拉遗址Quiriguá,正面是一位正襟而立的君王形象,侧面配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大概人类文明形态虽千差万别,但君王永垂青史的心态总相似。我还在Toniná见过更孤单的石像,孑然立于偌大的金字塔台阶正中央,有如在郑重欢迎,又似在锁眉警告,还像在潜心默祷,令人很难琢磨出它表情的深意。我注意到,在玛雅遗址附近的餐馆门口竟也像模像样地挡有一块小石像,为了给游客营造古境,淳朴的当地人也是费了一番心思。这令我想起中国守门的石狮子,大概古今中外文明之间偶尔也会灵犀相通。 危地马拉玛雅遗址Quiriguá7米高的石碑(网络图片) 立在Toniná金字塔正中央的石像 这些石雕如今赤裸着石色,过去却都身着五彩外衣。考古学家发现Yaxchilán的门楣曾被涂成蓝色,ChichenItza的石柱则是红、黄、蓝,Copán的Rosalila神庙曾是红、黄、绿。岁月像一位得道高人,不喜华丽,凡所经之处都还其一片素雅。 Copán的Rosalila神庙复原版(网络图片) 当然,也有岁月特赦之处。玛雅壁画正是,历经千年风雨,色彩犹存。最著名的玛雅壁画藏在Bonampak遗址金字塔腰间一栋不起眼的石屋内,在上世纪中叶被发现时曾经轰动世界。考古学家认定绘制时间约在公元7世纪。壁画填满了三个房间的内墙,所叙述的内容大致是君王的加冕、邦国的战争和俘虏的祭祀。很多局部画面模糊,像脱掉近视眼镜一样,需要眯起眼睛费力辨认。但若姑且“失焦”望去,不在意线条,只看大块色彩,最冲击心灵的则是那抹玛雅蓝。玛雅人在大地植物中寻到了模仿苍穹色泽的秘方,而调配出的颜色却比天色更灵动,属于梦境、幻想、记忆——一切游移不定、难以把握的事物,令人千年之后仍为之低回不已。 墨西哥玛雅遗址Bonampak壁画上的玛雅蓝 Bonampak壁画局部 Bonampak藏有壁画的石屋 本世纪初,考古学家又在危地马拉遗址SanBartolo发现了比Bonampak早近一千年的壁画。这壁画更具远古传说色彩,其中的神话故事可以溯源至玛雅古籍《波波乌》。其它玛雅遗址的壁画也各具特色,如ChichenItza的壁画展现了古时水上贸易,Calakmul的壁画记录了普通人生活场景,Cacaxtla的壁画则描绘了长长一面墙的战争史诗。 危地马拉遗址SanBartolo壁画复原图(网络图片) ChichenItza壁画(网络图片) 墨西哥玛雅遗址Calakmul壁画(网络图片) 墨西哥遗址Cacaxtla的长轴壁画局部 除了散落在现实里的,玛雅人还营造了心灵中的“微秘境”——玛雅文字。圆圆的方块字中,人与兽穿行其中,被各类秘符、数字萦绕,如一个个包罗万象的宇宙。阅读这些文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艺术的,沿着每一笔圆滑的线条、每一个带画面的偏旁,跳进字里行间游目骋怀,尽情发挥想象力去误解,去错读,于是一千个人眼中足以生出一千个版本的玛雅秘境。另一种是科学的,如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那样,解码字音、字形、字义,钻研一个符号究竟是表示一个字、一个词、一个短语,还是一个句子。这种阅读方式自然会过滤掉一层浪漫,人们读懂的往往是连篇累牍的战争记载和君王赞歌。 Palenque的玛雅文字 前一种阅读方式把玛雅人捧至仙界,后一种则将他们拽回人间。人们开始了解古玛雅人也同其它文明一样食人间烟火,在大大小小遗址间也曾上演过爱恨情仇。例如,在Calakmul和Tikal两大玛雅强国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旷世战争,最终Tikal惨败,从此一蹶不振;Toniná被称为“国王的囚室”,它曾捕获并斩首了多个玛雅邦国的君主,其中包括Palenque的一位;Palenque曾出现过“康熙盛世”,其伟大君主Pakal在位长达68年…… 不过,也就至于此了,更多的历史恐怕是罄“石”难书的,太多过往和故事都随长风和远云消逝,唯留一片寂寂的荒堞与杂草。那些一晃而逝的集体记忆,像是做了一场长长的梦。令人想起玛雅文明后期同时代的东方大词人苏轼那句感慨:“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不过,不论醒着还是梦着,能如玛雅人这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也不枉来世一遭。 雪暖暖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ermopana.com/bemptq/6117.html
- 上一篇文章: 一波特价发送中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