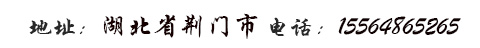留学大家说听美国桥水大学的归家人娓娓
|
归家人也是离家人 ——美国桥水大学交换心得 今天跟我们分享海外交流学习心得的同学是——15级汉语国际教育2班 李心羽 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出国留学念头的我曾经以为高考、大学、实习、毕业就是我人生的正轨,不会有任何的分岔路口,而如今我已然结束了8个多月的美国交换生学习生活,这或许就是人生,就是正青春的大学生应有的果断,而我很庆幸我做到了。人生中会有很多的八个月,也会有很多来来往往的朋友,或者可以称之为伙伴的短暂的同路人,但这八个月我体会到的是值得珍藏在心的“家”与“家人”。故事很多,很怕自己会遗漏一些精彩的部分,但是不急,我会娓娓道来。 首先提供温暖给国际生的是国际部,一个简称ISSS,念得时候如果把第二个S念错成I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官方交换生与学者办事处。虽然不清楚美国其他高校的情况,但就桥水而言,学校的师生对国际生和交换生在理解上区分度不大,所以刚到之初所有的交换生就被安排和所有的转学国际生以及一年级新生一起参加入学前的介绍讲座。特别要提一下的是,算上港台地区,这一学年中国这片区域来的交换生分别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以及香港教育学院。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但却说着汉语的学生们在与来自日本、韩国、英国、爱尔兰、法国、巴西、尼日利亚和伯利兹等国家的学生们一起参与到了国际部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从观鲸,到女巫镇,到“超级碗”橄榄球场,再到著名的“红袜队”棒球赛。总之,只要认准ISSS这个神奇的组织,总能参与到一些本土化的活动中去,极大地丰富了特别是亚洲学生的文化视野。 在国际部中有一位老师特别值得一提,杜老师来自中国香港,我与他相识要源于我曾经在桥水的两周修学游经历,他作为带队老师热情地快到了我和我的同学们,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友善和真诚将我再一次带到了这里。杜老师作为全球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常常发起以及参与到各类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他本身还兼有纽英伦华人历史协会副会长一职,致力于华人史研究已有30多年,毫不夸张地说波士顿的华人街上大部分的商家都认识或知晓他。也是因为他的带领,我有幸在校内和校外参与到了一些与美中关系以及美亚关系的论坛。最近的一次是四月份位于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成立二十年系列演讲,在听了各位亚洲问题专家深入浅出的探讨后,我更有幸见到了前澳洲总理陆克文,他演讲的题目是“习近平的世界观”,虽然他说的内容并不容易理解,而大多可理解的部分往往和曾经在国内上过的《马克思原理》内容一致,但这对于我来说总是一次很有趣的体验,能有幸和来自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同学一起聆听某国前总理关于亚洲问题的解读和讨论,我想除了知识面的拓宽,还有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第二个“家”,也是给予我最多温暖的地方叫做“ScholarHouse”(“学者之家”)。这个家的故事很长因为家里的人有很多,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也有来自宝岛台湾,很多人来自北京,当然还有苏州、杭州、武汉、西安,以及上海。这个家里最重要的一家之主是“吴妈妈”,所谓“吴妈妈”首先学者之家的住客年龄与我们的母亲相近,其次她总是在学者之家为我们烧制满桌的中国菜供我们中国师生解思乡之情,而她真实的身份是Prof.吴。吴老师是一位从内陆到香港工作的日语专家,她本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就读,后来赴日做了很多有关“日本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来美国之前,她已辞去北外日语教授的职位在港大任教6年之久,是一位十足的“学者“。特别幸运的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学者之家都只有吴老师一人入住,这里渐渐地就成为了我们中国学生的秘密基地,学生们也成为了驻扎在这里的“钉子户”。志趣高雅的来这儿喝茶聊天,住校外的没了吃食就借着“喝茶”的名字来找吴老师“蹭饭”,学业不繁忙的来这里组个桌游的小分队也是特别棒的聚会。总之,这些“吴妈妈”的“小猴子”只要有时间就会来叨扰“学者之家”。这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回忆:送别半年期的学者和学生、新年晚会、吴妈妈生日、学生生日以及最后的交换生饯别会。这里见证了太多的欢笑与眼泪,笑,因为快意,同胞间的文化认同,与课堂上若有若无的距离感不同,我们笑着揉面、包饺子、做饭,笑着在停电的元宵节吃着冷冷的火锅汤,笑是基本,笑是所有。哭,则有很多原因,有感动的眼泪,更多的是离别的不舍。吴老师哭着看完了我们特意为她拍摄并剪辑的生日视频,我们哭着送小伙伴上了去向机场的车。 当然,除了国际生的家、中国学者与学生的家,我还找到了美国的“家”。这第三种“家”更多的是习惯的养成。这里的交换生有半年期与一年期之分,所以,当第二学期开始的时候总能从刚来的半年期交换生身上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学期末的时候,学校里第二语言服务的调查中有个这样的问题:你刚来时,让你感到最陌生,最无法融入的是哪一点。我想无论多少人问,我都会说“Greeting”,其实说得更深远些,应该是如何沟通我所学的英语和美国人日常所使用的英语之间的鸿沟。 还记得初来乍到,在食堂、在路上、在课前,每当有人跟我打招呼,如“Howareyou”“Howareyoudoing”以及“What’sup”时,我总有种深深的无力感,有时甚至一时没法及时反应愣在当场。是的,来美国的目的之一,甚至是最大的目的就是语言的实践。作为一个专业与“语言学”相关的学生,我深知,学习第二语言中,在目的语环境中的参与程度,以及语言使用度是多么的重要,潜移默化的语言习得比课堂中的语言学习对于语言的获得更为有益。交流是一,和本地学生交朋友是二,两者相辅相成。但毕竟,语言是前提,处于第一学期的我,尽管在课上十分专注,时刻跟随着老师的思路与步伐,但常常也有话到嘴边无法确切表达含义的时候。尤其是在“英国文学”这门课,“如果对于美国学生都是相当困难的一门课,那么一个说中文的女孩去上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呢”,怀抱着尝试的心我全勤通过了整个课程,虽然最后只得了一个B,但是我已经相当满意,它真实地反映了我的学习状态和接受程度。我并不后悔,因为这正是我来这儿的初衷,在这学习的两个学期,更多地是体验,是去看看在国内看不到的世界,作为半个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所涉及的“英语”这个领域的东西,过多地是培养语言在听说读写上的技能,深化,熟练。而美国的英语专业必然不是如此,正如中国的汉语言专业也会去研究古文学,古汉语,美国的英语专业分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及爱尔兰文学等,而我因个人喜好偏向更源头、更传统的英国文学。当所有的古英语知识、宗教概念配合我相比美国英语专业学生而言相当有限的“英语能力”时,Everythingmessedup。 但一切都会慢慢变好,就像之前说的,语言能力是渐进的,而且随学随用,前一秒从A同学身上学习的表达可能下一秒就可以用来和B同学进行交流,这就是学习语言的乐趣。作为一个语言爱好者,我在桥水的两个学期修完了两节日语基础课。是的,说来是有些有趣,中国人来到了美国用英语学习日语。但对我来说,在美国学习日语是一段相当值得享受的旅程,当我和美国学生同学一门新的语言,那我们之间就不存在所谓的语言优势,甚至作为中国人对于日语系统中的汉字更为熟悉,成为了一大优势,总之,在我眼中,语言课是一个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学生处于同一平面学习的一个平台。 日语课也让我交到了很多珍贵的朋友,我的很多美国朋友都曾参加过或有兴趣参加去往亚洲的修学游团,所以他们对于亚洲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往往不仅对日语感兴趣,同时还对中文有着相当大的热忱。还记得在第一学期初的留学推介会上,我坐在上师大的摊位上无人问津,而旁边的台湾、香港、北京的大学却拥有几位有兴趣的人。当到了第二学期时,同时同地,我的checklist上却多了熟悉的名字。虽然最后很多因为学分转换、经济原因需要延迟来上海的旅程,但我依旧很高兴他们能被中国文化、被上海师大所吸引。当然最后,我的一位好朋友作为唯一一位留在名单上的申请者毫无疑问地顺利通过了选拔,即将在九月抵达上海,在我的学校、我的学院进行为期一学年的交换生生活。 除此之外,我还选了一些我在国内并没有机会,甚至也永远不会选择的课程,比如街舞和非洲鼓。学街舞的初衷其实是陪伴我那来自北交大的好友,她的舞龄已有两年,而我却为零。然而,实际上整堂课的同学里除了我的好友谁都没有接触过街舞这个领域,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学起,从最基础的Step开始,到黑人斗舞味十足的Brooklyn,再到需要用身体某个部位支撑起所有力量的Freezing。课程中的很多内容在一开始都有着让我望而却步的难度,但随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们互相之间的支持,大家还是坚持了下来,虽然课程只占了半个学期,它所带来的欢愉却是无法计量的。 另一项课程则是非洲鼓,这个课程已经存在很多个年头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课程所招收的对象不仅是BSU的学生,还有桥水镇上的居民,所以在课上遇到80几岁的老太太不稀奇,遇到同学的房东不稀奇,和高中生一起学鼓也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团队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成员们。一开始参与到这个团队的只有两名来自北交大的交换生,后来随着其中一位半年期的同学归国,剩下的一名同学又鼓动了我,我又鼓动了其他中国朋友们,到我们音乐会的时候,台上这个12个人的团队里,已有5名成员是中国学生。其实刚入校就听说过这门课程,一直以为只是枯燥而又繁杂的乐理课,对于自身专业并没有太大练习,或许会浪费时间,但直到我受邀去观摩了两位同学在上半学期的汇报演出,我才真正被非洲鼓的韵律和节奏所感动,在音乐部门的汇报演出中,有古典柔和的交响乐,也有唯美宁静的唱诗班,当压轴的非洲鼓登场时,除了焕然一新,更有振聋发聩之感。以掌击鼓,时而清脆,时而厚重,旋律错落有致,给听众带来一场原生态的视听盛宴。我从来没有想过音乐可以这样的鼓动人心,仿佛全场的观众都被带到了那起起伏伏的节奏中,身体和四肢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由自主地随着鼓音律动。而当我真正坐在那个舞台上开始学习时,我发现它的魅力更大于舞台下观众所能感知的,它的魅力更多地在于成员之间的互相配合。受课程性质所限,这门课实则不教授任何的乐理知识,成员们只需要熟记手法和旋律即可,在表演过程中老师会以特定的旋律作为变换的信号,以帮助成员转换到下一段旋律。经过半个学期的学习和排练,到学期末的非洲鼓音乐会时,我们这个全新的团队已能编排出5首曲子:Moribyassa,Tiriba,Salil,Kuku和Dununba,看着台下几乎座无虚席的观众脸上的笑容,台上的我也顿感应有的紧张已不知所踪。表演的最后,我们甚至现场教学,邀请了部分观众上台尝试与我们一起演奏,望着大家脸上的笑意,我收获了从所谓有的满足感,后悔自己晚了一个学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又遗憾归国之期以近在眼前。 在我“美国的家”这个概念中绝对少不了一位可爱的老太太Frances,她是我参与的第二语言服务项目中的交流搭档。在这个项目中,所有的搭档大多是生活在桥水镇上的居民,而我的搭档不仅家住学校图书馆旁边,同时也是BSU的退休员工,在我对于美国学习生活以及日常交流还一知半解的时候,是Frances带领我一步步地走近美国的校园文化,或者说是主流文化。还记得临近感恩节的时候,整个学校的学生全都离校与家人团聚,而我只能孤身留在宿舍里,很有“家徒四壁”的寂寥感,后来是正是Frances发来了邮件邀请我和吴老师等中国学者去她家体验感恩节大餐。和Frances家人们共度的那个晚上可以说是我上半学期里最温馨的时刻,那天下午我到达得很早,她的小女儿和巴西丈夫刚刚从纽约风尘仆仆地赶来,于是我们4人开始了畅谈,Frances告诉我她特别感恩的是在很大的年纪还能有机会再做母亲,即使不是生理层面的母亲,我正还疑惑,正巧一个略带亚洲面孔的男生出现在视线中,原来她收养了一名韩(国)墨(西哥)混血的男孩。听Frances讲自己的故事是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她总会笑意盈盈地看着你,眼中带着柔柔的光,你甚至都分不清那是长者的智慧还是善人的福音,只能被她的目光牢牢地吸引,仿佛正在接受神圣的洗礼。 说了那么多我的家人们,最后还是很想说说身处在这些家庭中的自己。拥有一段超过半年的独自生活的经历即使艰难,但还是坚挺过来了,作为唯一一个来自上海师大,来自上海的交换生,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很多小家庭对我来说是都是特别骄傲的事。在这8个月多的时间里,我也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心境在变得不一样,如果说在上海的我总是忙碌于学生工作、学业成绩、各项实习之中,8个月我是真正地为自己而活,真正充实而有意义地过着我的人生。选自己真正喜欢并且感兴趣的课程,每一节课程都认真而不被打岔地去完成。当大部分的交换生都在8个月中增了不少体重时,我坚持健康饮食,每天定时定点地去健身房和游泳池,成功地在美国瘦身近10斤。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蜕变,都是在美国,在桥水这8个多月的时间里所赋予我的最美好的记忆和经历。 是归家人也是离家人,我将带着离家的别愁和归家的喜悦继续前行,我知道的,只要时钟还在运转,我们再次相见的时间就不会太远! 下次再来讲述,也欢迎大家的分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ermopana.com/bemptq/2454.html
- 上一篇文章: 攻略组出品ldquo文化圈争夺战
- 下一篇文章: 高考刚结束,这些长着中国脸的外国人,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