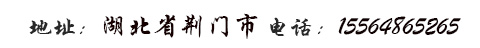虑得居安健我印象中的印象派
|
我印象中的“印象派” 文\安健资深媒体人文史随笔专栏作者、中国南社研究会会员何谓赏心悦目,艺术审美“传导”所致也。去年和今年,西方艺术的重要流派“印象派”的绘画,两度从欧洲艺术之都巴黎来到上海,在艺术爱好者中引起极大的轰动效应。 笔者对印象派情有独钟。我的西方艺术启蒙之路,就是从印象派开始的。文革后,我买的第一本西方艺术的书,便是关于印象派的,买的第二本依然是印象派的。这两本书是年版的《谈印象派绘画》,作者杨蔼琪;版的《印象派的再认识》,作者吴甲丰。这也是文革后最早出版的介绍印象派绘画的两本小册子。从那以后四十多年,我始终对印象派一往情深,陆续买了许多相关的画册与论著。直至这次在沪上观摩了《莫奈与印象派大师展》,展览的画家都是我梦幻中的偶像,除主角莫奈外,还有马奈、德加、毕沙罗、雷诺阿、希涅克、西斯莱、莫里索等。面对61幅大师的真迹,震憾之余,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慰藉,犹如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单相思。 下面谈谈我印象中的印象派,作为这次观展的随想。 印象派领袖:马奈乎?莫奈乎? 马奈与莫奈,谁是印象派领袖?这个问题要分时间段来谈。印象派最早的领袖无疑是马奈,他是印象派这个圈子最初形成时的带头大哥,那时印象派的众画家还都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而马奈已在艺坛崭露头角,虽然不受学院派待见,屡屡落选于官方沙龙,但他已名声在外,有了自己的画室和经纪商。 (拉图尔:《巴迪侬画室》) 上面的这幅画,很好地反映了当时马奈的声望以及他身边的艺术圈。此画是马奈朋友拉图尔所绘,画中马奈在他巴黎十七区的巴迪侬画室作画,他是画面的中心,坐在马奈侧面的是雕塑家阿斯特鲁,充当模特。身后站着一帮圈内好友,站在马奈背后左侧的是来巴黎旅游的德国画家,不太有名。站在马奈右侧,带着帽子,头在墙上画框里的是印象派画家雷诺阿。他右边眼睛朝着正前方的是作家左拉,左拉肩右是拉图尔的友人。画中身材最高的是巴齐耶,是印象派中的革新家,他与莫奈、雷诺阿和西斯莱并称为印象派中的“四人帮”,他们四人同出于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格莱尔门下,后来又都受到马奈的影响。巴齐耶的背后是莫奈,他在画面最右侧的边上,只露出一个头,那时莫奈尚未竖子成名,低调地站在后面。当时大家都围绕着落选者沙龙,而马奈是这个沙龙的主角。 (马奈《朱庇特与安提奥普》。展品) 早期马奈对莫奈的影响较大,莫奈画的一些作品与马奈的风格相近,如莫奈画的人物画《卡米耶》与马奈的《杜乐丽花园音乐会》中的人物形象相类似。漫画家吉尔看了莫奈画的《卡米耶》,感慨地说:“莫奈还是马奈?我们要感谢马奈启发了这样的莫奈。” 一晃没几年,莫奈的画艺突飞猛进,年,莫奈的作品《绿衣女子》第一次入选官方沙龙,并获好评。他顿感自信心爆棚,便开始了进一步创新,尝试了室外自然光下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逐渐替代了马奈成为印象派画风的领军人物。印象派之名,也是因为他的一幅作品《日出·印象》而得名,故莫奈被尊称为印象派风格的创始人。 (莫奈《日出·印象》) 原本马奈的画风就不是与印象派一路的,他仅是早期印象派的精神领袖而已,并不是风格上的倡导者与领路人。所以他一次也没有参加印象派的画展。当印象派画风形成后,他便分道扬镳,将领袖地位“禅让”于莫奈,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这次在上海外滩一号观看的《莫奈与印象派大师展》,均为巴黎玛摩丹莫奈博物馆的藏品,该馆成立于年,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莫奈作品的博物馆。这次共展出了20幅莫奈的杰作,占整个展览作品的三分之一,涵盖了莫奈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如早中期的《漫步阿让特伊》《圣拉扎尔火车站》《荷兰的郁金香田》《吉维尼的黄色鸢尾花》,晚年的巨幅《睡莲》《紫藤》和《日本桥》,尤其是睡莲,有好几幅,这是莫奈晚年的标志性作品。站在画前,驻足欣赏,让人留连忘返,大呼过瘾。懂得美,享受美,能够让人升华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 谢谢莫奈,谢谢玛摩丹。 (保罗·波林《莫奈雕像》,展品。) (莫奈《漫步阿让特伊》,展品。) (莫奈《圣拉扎尔火车站》,展品。) (莫奈《睡莲》,展品。) (笔者在展览现场,欣赏莫奈作品。) 印象派“隐形领袖”毕沙罗 毕沙罗在印象派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年龄最大,宽容随和,人缘最好,他也是唯一参加了印象派所有八次联合画展的人,他是印象派风格最坚定的基石。印象派是一个松散型圈子,莫奈成为领袖后,因其过于傲气,好几次差点与印象派的一帮小兄弟闹翻,盖尔波瓦咖啡馆里总是一片喧嚣的争吵声,每次都是毕沙罗出来打圆场,才平息了一次次矛盾的激化。尤其是莫奈与德加两人积怨甚深,从艺术分歧,到人品指责,闹得不可开交。但毕沙罗总能像润滑剂那样,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稍有名气的艺术家最难缠,自恃甚高,互不卖帐。其时的印象派画家正是如此,个个名声不大,脾气不小。 每一次印象派画展的策划与筹备工作,也是毕沙罗出力最多。当展览主题与邀请名单有异议时,毕沙罗都会从中协调。但麻烦事仍不少,谁能参展?作品布置的前后次序与位置好坏?每每都会引起激烈的争吵。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执,在举办第一次印象派联合展览时,毕沙罗便建议制订一些规章条例,以便照章办事。但艺术家都是散发性思维,不善于搞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毕沙罗抓耳挠腮,想了数天,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无奈之下,他便从常去的面包店拿了份面包师同业公会的章程,然后作了些相应的修改。大家七张八嘴争论了一番,总算达成了协议章程。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过展览而销售出去的作品,将缴纳十分之一的款项作为共同基金。二是展览时作品的布展位置,均通过抽签决定,让每次展览的好位置对大家都机会均等。三是参展人员由招募小组邀请。首届展览的招募小组由印象派主要创办人莫奈、德加、毕沙罗、雷诺阿、西斯莱、莫里索组成。这些章程约束了艺术家散漫而又极其自尊的个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为以后印象派的活动与展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毕沙罗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 印象派这个圈子前后维持了二十年左右,很不容易,毕沙罗虽非群主,但从中发挥了粘合剂作用。所以说毕沙罗是印象派的隐形领袖,一点也不过份。 (毕沙罗的扇形画。展品。) (毕沙罗《步道雪景》,展品。) 印象派的“另类者”德加 说德加是另类者,因为他是印象派中唯一不在室外作画的画家。之所以称印象派,就是因为这些画家在大自然中凭着真实的印象,描摹出阳光下色彩斑斓的画面,所以也把印象派称为户外画派。其实印象派的前辈巴比松画派,比印象派早走入户外,柯罗曾高呼“大自然先于一切。”但巴比松画派的用光与色彩,还是较为传统,远不如印象派那么强烈而富有特色。 那么德加为何不愿把画架移到户外呢?为何要违背印象派的宗旨呢?究其原因,是他三十多岁就患有眼疾,畏光,不适应阳光照射,无法在户外绘画。所以他选择了坐在黑暗的剧场中,描绘舞台灯光下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女。 德加毫无疑问是世上观看芭蕾舞最多的画家,巴黎歌剧院的芭蕾演出,他几乎从不缺席,一生画了多幅芭蕾舞的画。德加出生于富裕的银行世家,从小就养尊处优,不像大部分印象派画家处于贫困状态。而频繁出入巴黎歌剧院,似乎是他身份的象征。其实德加最早去巴黎歌剧院,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在剧院交响乐队当演奏员,与芭蕾舞演员很熟,他向德加讲述了这些年少的女演员舞台生涯之艰辛,优雅舞姿的背后,是无数辛酸而令人泪奔的故事,洁白的绑带,解开后是血迹斑斑的伤痕。这些引起了德加观察的渴望。巴黎歌剧院那时每周有三次演出,买了通票的观众,平时可自由出入演员的排练场,甚至休息室,还可以到后台观看预演。这些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方便极了,如鱼得水。德加经常购买包厢的座位,但他却很少从舞台的正面描绘芭蕾场景,只有著名的《舞台上的舞者》《执花束谢幕的舞者》等少数几幅,绝大多数是舞女排练或休息的场景,剧院的排练厅是德加去得最多的地方。从他作品的画面看,似乎德加白白浪费了昂贵的包厢费。 (德加《舞台上的舞者》。) (德加《舞蹈教室》。) (德加《两个舞者》。) 德加的另类,也包括他一直否认自己印象派的身份。尽管他是印象派圈子里的中坚人物,他参加了印象派画展总共八届中的七届,仅次于毕沙罗。但他却一直对印象主义的绘画理念给予抨击,他认为过多注重户外太阳下的光影效果,会损害绘画的结构与线条,他希望画家返回室内。他曾忿忿地说:“警察应该开枪射击这些搞乱乡间宁静的成排画架。” 德加的另类,还包括他对女性具有两面性。德加笔下描绘的对象大多是女性,除了舞女,还有浴女,梳发女,洗衣女,烫衣女等,观察入微,形象生动。德加一生描摹女性,由衷热爱他笔下的女性。同时又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抱有强烈的偏见,导致他终生未婚。在女性中只有一人例外,她就是美国印象派女画家卡萨特,成为了德加唯一的红粉知己。原因是他们俩都来自于富裕的家庭,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共同的习性与修养。卡萨特定居巴黎时,她与德加的工作室都在蒙马特尔大街,靠得很近,时常往来。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是不婚主义者,交往没有心理负担。 (德加《烫衣女工》。) (德加《亨利·胡厄画像》,展品。) 印象派的“背叛者”梵高 无论把梵高归类为印象派或后印象派,都是勉强的。梵高年春从荷兰来到法国巴黎时,印象派正处于分崩离析之际。这一年,对印象派来说不是一个好年头,第八次印象派联合展览就像是一顿散伙饭,宴席散后,大家各奔东西,分道扬镳。梵高之前与印象派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也无资格参展,只是应毕沙罗之邀,参观了这次展览。 梵高认识毕沙罗,是由于他弟弟提奥的介绍。提奥当时在巴黎蒙马特尔大街开了一家小画廊,代售梵高以及印象派画家莫奈、毕沙罗、德加、西涅克、高更等画作。提奥与毕沙罗较熟,便将梵高介绍给他。于是毕沙罗邀请梵高来巴黎参观印象派的第八次联合展览,这也是印象派的最后一次集体献艺。梵高对展览作品的丰富色彩与光影效果,有着强烈的感受。毕沙罗耐心地向梵高讲述了自己及印象派的绘画理论与技巧,对梵高触动很大。梵高之前的画面都较为暗淡,受巴比松画派大师米勒的影响较大。自从遇到了印象派,此后他的作品变得明亮了许多,色彩感也更强烈。毕沙罗第一次见了梵高,就立刻预感到此子非同凡可:“这个人会变成疯子,或者把印象派画家们远远甩在后面。”毕沙罗的这两个预感,都被不幸言中了。 (梵高早期作品《沼地里两个女人》。) (梵高《星光夜》。) (梵高《向日葵》。) 梵高在巴黎的两年中,一直追随着印象派的风格,很入迷。另外,他在巴黎也收获了与高更的友谊。离开巴黎后,梵高来到法国南部地区的阿罗,那里的景色使他想起了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色彩,以及日本浮世绘明快的轮廓线。梵高的画风又起了变化,背叛了印象派的风格。他给弟弟提奥写信道:“我在巴黎所学到的东西现在已离开了我,我恢复了在知道印象派之前我曾有的想法。如果印象派画家们指摘我的创作方法,我将不会感到惊奇,因为我的创作方法与其说是被印象派影响,还不如说是被德拉克洛瓦的思想所滋养。因为,我不是想正确地重现我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是较随意地使用色彩,以便更有力地表现自我。”其实这也是梵高与印象派“割席”的自白。 在南部地区阿罗,梵高与印象派的另一个离经叛道者高更相逢,一起作画探讨,不亦乐乎。但这两位离经叛道者的个性都过于强烈,日子稍长,便互不相容,争吵不休,梵高更是大动肝火,导致神经失常,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吓得高更离他而去。 (梵高《耳缠绑带的自画像》。) 自此以后,梵高在精神病院呆了一年,又在瓦斯河畔的奥维小镇呆了二个月,在这短短的一年多里,他的绘画艺术达到了高峰,但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年7月27日下午,在留下了那幅著名的画作《麦田群鸦》后,他也在那片麦田里开枪自杀了,三天后离世。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作品,贫病交加,身后却暴得大名,艺术史上流芳百世。假如梵高地下有知,得知如今他的一幅画便能身价超亿,恐怕又会被吓成精神病,一不留神,另一只耳朵也会被他割掉。 (梵高《麦田群鸦》。) 印象派的“后援”左拉 左拉,法国著名小说家,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同时他又行走在艺术评论的地盘上,推动着艺术新潮流冲锋陷阵。 左拉与印象派的关系,缘于塞尚。他们两人是法国普罗旺斯名校波旁中学的同学,写《茶花女》的小仲马也是他们的前辈校友。在学校里,左拉与人打架,塞尚挺身护卫比他小一岁且瘦弱的左拉,事后左拉提了一篮苹果送给塞尚,表达谢意。后来塞尚成为大画家后,总喜欢在静物画中画苹果,被人笑称为“苹果的代言人”。据说就是因为当年左拉送给他的一篮苹果,让他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左拉后来因塞尚的介绍,认识了不少印象派的画家,并成为朋友。左拉早慧,成名较早。在印象派初期,除马奈外,其他画家还没出道时,左拉已是崭露头角的作家与评论家了。年左拉出版了艺术评论集《我的沙龙》,并将该书献给了塞尚。 (塞尚《苹果与水壶》。) (塞尚《牛奶罐和苹果》。) 其实左拉并不太欣赏塞尚的画,左拉最欣赏的是当时印象派的大哥马奈,我书架上有一本书,叫《印象之光:左拉写马奈》,书中收集了左拉对马奈的多篇评论。尤其是马奈在艺术道路上遭受曲折时,左拉总是站在他身后的坚定支持者。马奈的代表作《奥林匹亚》展出后,画中的祼女从以往的维纳斯之类的女神,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妓女形象,大大刺激了艺术卫道士的神经,受到了学院派与媒体潮水般的攻击,刊物与报纸上充斥着对马奈的嘲讽与讥笑。左拉则站出来力挺马奈,撰文称赞马奈的《奥林匹亚》是“一幅伟大画家的作品”。左拉还写道:“我们前一辈人嘲笑了库尔贝,到了今天,我们都在他的画前流连忘返;今天又在嘲笑马奈,将来又该在他的画前出神羡慕了。马奈先生一定是巨匠,我对此坚信不移。”左拉不光赞扬马奈,他还收藏马奈的作品,自称是“马奈的一个狂热崇拜者”。马奈特地画了一幅左拉的肖像,送给他,以表示感激。从画面看,就知道这是左拉在马奈的画室作客,墙上有马奈《奥林匹亚》的小样,还有当时印象派画家痴迷并收藏的日本浮世绘作品。左拉坐在沙发椅上翻阅书籍。场面表达了两人的亲近关系。 (马奈《左拉肖像》。) 遗憾的是,左拉与印象派的友谊没能善终。原因之一,是左拉称赞印象派时,把过多的笔墨给了马奈,引起了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不快。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于年发表了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中的一部《杰作》,并分送给好友,结果其内容触犯了印象派众人,尤其是老同学塞尚。左拉的小说描绘了一群画家,有过抗争,但更多的是无奈与困顿。其中的主人公自诩为天才,却一事无成,潦倒终生,最终在自己未完成的巨幅画作前自杀。客观地说,左拉的描绘也是印象派当年的真实状况,并预示了梵高四年后的悲剧。但当时塞尚认为影射的是他,十分恼火,于是给左拉写了封“感谢信”,感激他的赠书和多年来的友谊。其实这是一封“哀的美敦”断交书,两人从此互不往来,形同陌路,摇曳了三十多年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了。 后印象派的“命名者”弗莱 爱好西方艺术的人,大都知道印象派这个名字的来历,最初是因媒体嘲讽而得名。印象派第一次展览时,差评甚多,有人说这些画家把几管颜料装在手枪里,然后打上画布,签个名就完成了。也有人说,这些画是仅凭印象的涂鸦,至多只能算是草稿而已。有人看了莫奈《日出·印象》模糊的画面,以为自己的眼镜片有问题,拿下来擦拭后,再架到鼻梁上,发现仍然是模糊的,大呼上当。于是有位叫路易·勒罗瓦的评论家在《喧噪》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印象主义的展览会》,于是“印象派”之名不胫而走。 而“后印象派”这个名称的来历,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它是一个学者苦思冥想杜撰出来的。这个人就是罗杰·弗莱,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 印象派与后印象派,这两个名称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印象派虽因媒体嘲讽而得名,但被嘲讽的画家们也认可了这个名称。而后印象派画家,他们生前并不知道这个称号,是死后被人追加的。至于他们是否愿意头上顶着“后印象派”的帽子,也无从得知,塞尚他们无法像德加那样直率地否认自己是印象派。因为得名之时,他们已成为“先烈”,无法开口了。 后印象派的代表人物是塞尚、梵高和高更。其实“后印象派”这个称号,最初是弗莱为塞尚一个人量身定制的,但既然要称派,就只能再捎带几个。所以梵高与高更,在弗莱的著述里只是塞尚的伴郎与陪客。对于一般艺术爱好者而言,梵高的名声似乎比塞尚更大。而这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若从艺术成就而言,两人各具辉煌。若从艺术史而言,塞尚对后世艺术的影响更大。所以,梵高更受广大爱好者、拍卖行和博物馆的宠爱,而塞尚更受他身后的画家同行和现代艺术史家的宠爱。 如果说印象派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的桥梁,那么后印象派,尤其是塞尚,则为现代艺术开启了大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涌现出的各种艺术流派,如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塞尚的影响,塞尚的经典代表作《圣维克托山》,成为被现代派艺术家争相朝拜的“圣山”,所以塞尚被尊称为“现代艺术之父”。艺术大咖马蒂斯的一句话最能概括,他说:“塞尚是我们所有人的导师。” (塞尚《圣维克托山》。) 所以说,弗莱的所作所为,并非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他对后印象派的命名与阐释,为西方艺术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后来者提供了思维和审美的路径,充当了现代艺术乐园的向导。塞尚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而弗莱则被誉为“现代艺术批评之父”。 塞尚与梵高,生前身后两重天。生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身后却成了万人迷。他们能够咸鱼翻身,这与他们身后遇到弗莱这位“迷弟”是分不开的,不然这些艺术明珠还可能被埋没多年。弗莱是第一个以“后印象派”名义于年和年两次在英国举办专题画展的策展人,展出了塞尚、梵高、高更等人的画作。他将展览定名为后印象派,主要鉴于两点,一是时间概念,后印象派风格的形成晚于印象派。二是艺术概念,这个“后”是在风格上对“前”的反叛与超越(所以林风眠曾将“后印象派”译成“反印象派”)。然而,弗莱策划的展览选对了画家,却选错了国家,当时欧洲大陆对岸的英伦,在艺术观念上要比法国、荷兰落后保守一大截。所以,后印象派展览刚一开始,弗莱这位策展人就被英格兰人骂作艺术诈骗犯,说展品是一堆艺术垃圾,塞尚是“一个弄错了职业的屠夫”,并叫嚣要将弗莱定罪法办。来势汹汹的舆论,比当年印象派在巴黎展出时还要厉害得多。 (塞尚《玩纸牌的人》。) 然而,这时的弗莱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子,他作为著名艺术评论家,在欧美艺坛得到广泛的认可。同时弗莱还是资深艺术品鉴定家,是许多著名收藏家的掌眼人。最让人刮目的是,美国巨富、金融寡头摩根财团的掌门人J.P.摩根,聘请弗莱作为他的艺术顾问,身兼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的J.P.摩根,还建议大都会博物馆任命弗莱为博物馆高层管理兼绘画部主任。 有了摩根财团为弗莱“背书”,以及弗莱个人在博物界与艺术鉴定界的地位,同时他又通过艺术评论坚持不懈地为后印象派鼓与呼,不到十年,塞尚与梵高的作品就从人见人弃的“垃圾”,转眼变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欧美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如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以收藏印象派与后印象派作品著称,这些都与弗莱当年的功劳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在欣赏塞尚、梵高等人的画作时,不能忘了这位幕后英雄罗杰·弗莱,请记住他的名字吧。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ermopana.com/bemptq/11618.html
- 上一篇文章: 除了蝙蝠侠贝尔,雷神4几乎找不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