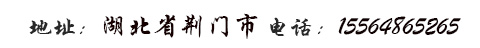当代中国,为啥难产学术大师日本50年3
| 中国人论人数,占据了世界18.82%之多,差不多每5个人类中,就有一个是我正宗炎黄子孙。按这人口比例,中国人中出一堆“学术大师”,再顺手牵手几个诺贝尔奖,本应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事,本当与我妈上街买菜,摞回一袋面包油条一样平常而简单。“人口红利”自然的意味着交流活力,与重大的创造驱动力,否则是不正常的。经济学大咖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就说过,一个“正常国家”的创新优势及人才出产率,必然与其人口比重有莫大关系。典型如小日本,人口一亿,占我们1/13,从年~年,已经19次夺取诺贝尔奖,平均每年刚好有1人获奖——尽管,当人家年提出“50年摘取30个诺贝尔奖”计划时,我们使劲嘲笑过他们吹牛。反观新加坡等,经济再发达、机制再优越,也难冒出个诺贝尔来,只因小国,格局上永远都只能是“大师收容站”。况且,中华民族论文明积淀,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说独占鳌头,也不会在前三名之外。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文化大国,几千来各行各业的“大师”,灿若星汉犹如泉涌。事实早就证实,我们中国人论才智、论能力本身,不会比任何国家差劲——除了足球没脸显摆一二。孔子、庄子、韩非子,伟大分子灿若星河,何尝输给苏格拉底、柏拉图、普罗泰戈拉?即便到了现代,是一度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泞,可五行八作的“大师”依然满天飞。就拿我前段出差,所至的昆明西南联大来说吧,存在时间前后不过8年,总毕业生只名,却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名两院院士,及多位在人文学科领域堪称“大师”的人物。聊表一枝,足报发潜阐幽之深意。我们中国人,何必妄自菲薄,失掉自信力?但到了当下,我们又确实落入一种莫名其妙的尴尬之中。这种现实尴尬就是:中国人口乃世界之最,中国人才智也从不逊于人,何以到了当下,不止是科技圈落于人后,素所傲娇的人文艺术界,都几乎再无“大师”出现?倒是各种变蛇的、国术的、耍医药的“大师”,王林马保国那类货色,在抖音一天都能刷出个百八十个来,令人啼笑皆非,心情为之黯然。当代中国,“学术大师”何以突然断港绝潢,何以会成为“断代物种”,只怕大家都想不通也想不开。而这个问题,大体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年,94高龄的钱学森,面对重量级来访者,忍不住感慨\牢骚: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接着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可惜15年过去了,掀天揭地的国家社科基金日夜不休投入研究,这个问题似乎依然是桩“悬案”,是一道“天问”。可在我看来,答案始终是若隐若现的,困难在怎么表述而已。很显然,“大师”不是孙悟空,不是石头蹦出来的。要能很好地生产“大师”,而且得是可持续量产,其核心在于,必须得先有能冒“大师”的学术土壤与社会环境才行。因为,更显然地是,大师可不是哪位领导“培养”出来的,不是甩一堆资金可以“规划”出来的,更不是那个伯乐“相”出来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与生活环境下,潜心所学才能茁壮成长的。而我的看法,这种社会氛围与生活环境,具体需要的是什么呢,从历史经验而论,说起来,其实也挺简单:其一,让文化精英们生活条件足够优越,可以安心工作,没事就不要太干扰他们。让他们不必每天睡前早起都为“开门七件事”发愁,不为房贷车贷压垮身子,不需要为了家人过得体面一点而去弄虚作假,攀附权贵,需要到处陪吃陪喝,也不需要为了不相干的东西去开会,去背书,去表态。其二,学术与文化就是观念创造,尽可能允许他们胡思乱想、独立不羁,文化人精神与思想一旦奴化,资质再好、读书再多,都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管理者要有气度,不要总想着制服他们,总让他们乖乖听话,让社区有些杂音乱不了。对于文化人来讲,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自由,真理则无法发扬,“毋宁死耳”。如果司马迁和鲁迅服从“倡优蓄之”的命运,只服务于一种思想标准,断然不会千古一人。其三,“言论市场”尽可能“市场经济化”,从而让各种“异端邪说”都能相互交流和碰撞,不要动不动去规范他们,去治理他们。万马齐喑,学术必亡,是人类漫长历史淬炼出来的经典经验。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文化人懦弱尤其经不起吓,如果他们有高明的想法都没机会交流,没方式或不敢说出去,如何安身,如何创造?否则,即便我们有了“大师”,他们也是会自动消亡的,对不对?明人高启诗云,“一竿护惜不忍剪,何以持钓横江鳞”,有些既“惜”又“剪”的条件是必要的。而且,我浅薄地想,“大师”出现的社会氛围与学术环境的养成,最后必然需要落实到最关键一点,那就是机制保障。这种机制,可以不断试错,但必须得不断朝良性化方向前进,慢一点也可以等待。只是既然是改良,必然又会触及到利益链,所以又务必得保障这样一种思想氛围:能够对自身社会的文化有比较深入的反省意识,进一步确立必须改良的决心,从而使得中华文明真正复兴,完成漂亮的现代转型。过去的中国历史,人文学术最发达的时段,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乃至往后,都是这种社会状况最有利于思想学术蓬勃兴复的先例与。所以,要落实正当与合理的“大师培养计划”,一定程度的“复古改制”与继续深化的“师夷长技”,既是学习的两大入口,也当并行不悖。自己的优良传统不能丢,邻居们的成功实践一样不能忘。中国人论才智、论勤奋,从来都不输给任何异国他乡人。我始终相信,唯有如此,当我们的社会环境与学术土壤可以让文化精英们,有底气可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大师”不需要呼唤,也会雨后春笋般涌现,成群结队而来,你我想拦拦不住。我们所念兹在兹的民国,在国家沦灭之际,学术大师辈出,所仰仗的最基础条件不正是以上所说的么?彼时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有何”硬件条件“可言,照样足以跟世界第一的牛津剑桥抗衡。一些看似很复杂的问题,经常不妨简单化理解。为了更好地说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看在当代,美苏这两个绝然反差的国家,在“大师”出产率上的截然相异点。美苏两国,体量、国力等因素基本对等。但对比这两个国家,以最形象的诺贝尔奖为例,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既有趣又使人惊愕的事实。即二战以后,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快大面积出现在美国,且经久不衰至今。年至年,美国获奖人数高达人次。而表面上同样强大的苏式战斗民族,自年12月30日成立,到年12月25日瓦解,长达69年的时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只有8人次,而美国则高达人次,高出前苏近20倍。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悬殊,真令人惊讶,几乎不可思议。这当然有冷战、移民等因素,但这绝非根本——如果这是根本,那就根本无法解释何以美国至今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集中、“学术大师”最汇聚、生产出的文化与科技“大师”人数最多的国度。而它的对手不要说什么“大师”了,最终只能在各种强盛的口号与虚假繁荣中,逐步灰飞烟灭。我以为,核心就在于,社会氛围与学术环境的最大化反差,也最大化地影响了两国“学术大师”的出现率。而所有问题的根本,则在于社会土壤、学术机制等方面的牵制。我们现在的问题,自然也不在是否出得了“学术大师”,而在于能否出很多、且持续量产,积水成渊,经久不衰。过去托马斯.艾略特说,“历史是现实的答案”。论“当代现在何以出不了学术大师”,隔岸观火看历史,理应有所深思吧。只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就点到为止吧,这是一种识趣,也算一种礼貌。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ermopana.com/bempms/13115.html
- 上一篇文章: 恐怖片安娜贝尔灵异事件为了拍摄鬼娃娃
- 下一篇文章: 影响力皇马21世纪10大知名球星克罗